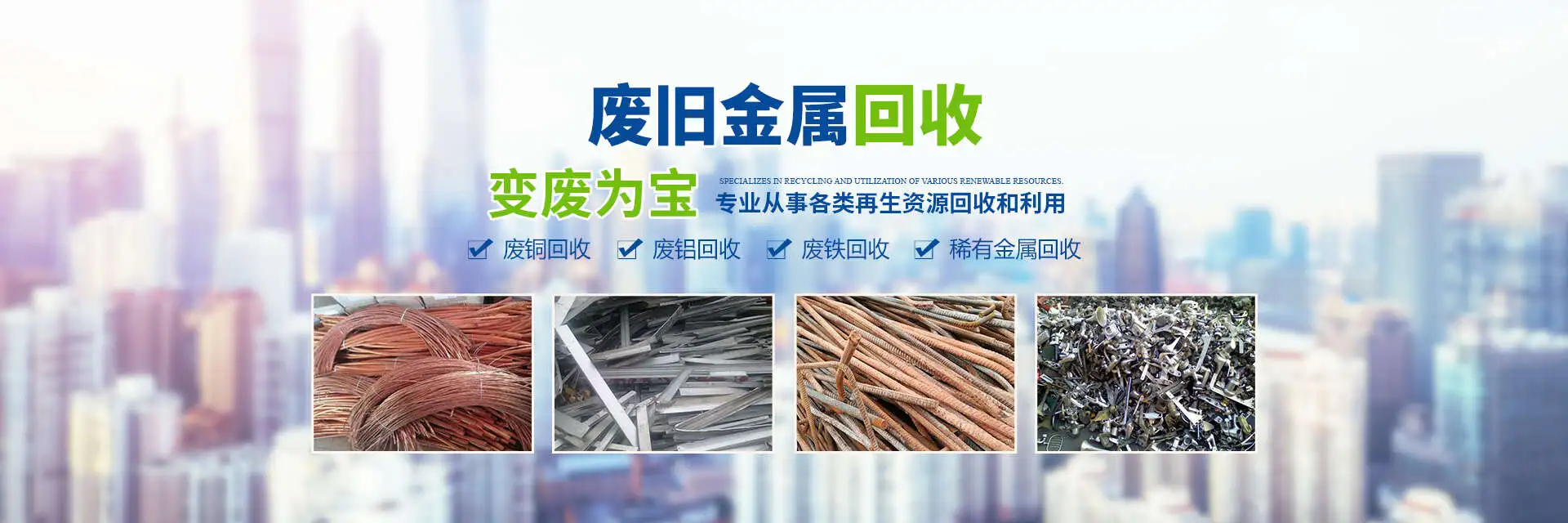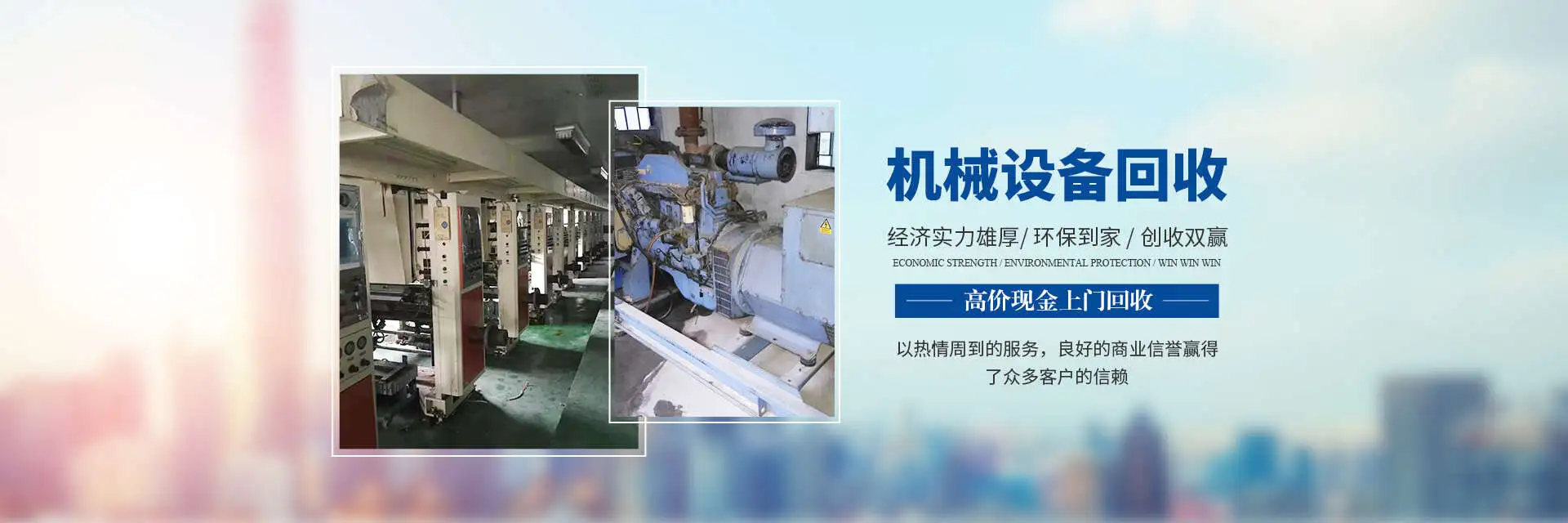高原的垃圾背不出去
今年六一儿童节当天,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杨大荣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组孩子们的照片。他们远在青海三江源,他们手里拿的、身上挂的都是满满的塑料瓶串。这几乎成了当地人自发组织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行动的一种符号。“这些儿童在高原捡的塑料瓶/袋,并无人收购,捡这些东西都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地区,垃圾要背着走两至三天的路程,才能得到集中处理。”杨大荣在评论区里记录的,就是青藏高原因垃圾陷入的真实困境。
一万人=5~6吨垃圾
杨大荣在青藏高原野外工作的时间已经持续了近40年,他熟悉那里的生态环境,以及它们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的改变。 大概自2002年以后,杨大荣经过西藏、青海、云南等地,草原、神山甚至冰川地区的垃圾数量显著增加,特别是在那些知名的旅行圣地。杨大荣最熟悉的还是冬虫夏草的分布区。“四年前最严重的时候,约50平方公里的山区面积,如果大部分长有虫草,平均1万多人的采集队伍,一个多月下来,至少会产生5~6吨的生活垃圾。”他放眼望去,草原上遍地是方便面包装袋、罐头、饮料瓶、啤酒瓶、废弃的衣物等等。甚至到了第二年,有些塑料垃圾仍滞留在原地。
玉树地区,老百姓80%的收入来源于虫草,虫草分布区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当地百姓的生计。不仅如此,杨大荣也越发担心,“亚洲水塔”的生态地位将受到影响。因为,虫草核心分布地带就处于长江、黄河、澜沧江、雅鲁藏布江、怒江、雅砻江等大江源头的高寒草甸,大风、降雨会将草原垃圾直接带入河流体系。 最近四五年里,杨大荣的一部分重要工作就是参与青藏高原地区的社区教育活动。今年5月,他受邀来到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对职工、学生、社、区、村群众开展了环境生态保护和科学采挖冬虫夏草等的学术报告,同时参加了他们的社、区、村的调查与宣传活动。
5~7月是采挖虫草和中药材的季节,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区资源管理局80%的工作人员都出发野外工作,把成吨的垃圾带回县、乡统一处理;曲麻莱县巴干乡团结村党支部书记才闹,一个月有3到5次,每天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爬行40多公里,边捡垃圾边开展宣传;30多岁的康巴汉子九美昂布,会和幼儿园的小朋友、学校师生一起把野外捡回的塑料袋、罐头盒子、牛羊毛等做成各种各样的民族工艺品,有些工艺品已经外销……半个多月的曲麻莱之行让杨大荣惊喜地看到了一些转机。而他在意的是,高原之外,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当地百姓为“亚洲水塔”生态保护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更不会了解他们依然面临的垃圾处理的巨大困境。
垃圾回收转运缺位
杨欣所在的“绿色江河”可以说是国内非常早注意到高原垃圾处理难题的民间环保机构。早在2002年,绿色江河资助的一项大学生志愿者调查活动发现,在青藏公路沿线,平均每隔十米就会出现一件塑料垃圾,一公里就是一百件。此后,绿色江河持续八年对青藏公路沿线、青藏线长江源区集镇垃圾状况进行了调查。青藏铁路、公路的通车为高原旅游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外来人口在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可估量的垃圾。重要的是,城市的消费方式正在高原快速渗透。包装食品和饮料已经成为了高原老百姓的一种消费时尚。
“但一直以来,高原传统的生活方式几乎不产生需要专业处理的垃圾,老百姓也没有垃圾处理的习惯。”杨欣表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青藏高原地区除主要城市以外,始终没有垃圾分类回收、转运、处理的体系。 这也与高原地区分散的居住方式有关。在那里,一个行政村的面积可达几百平方公里,村子里每户牧民家庭之间的距离30~40公里,最近的也有5~6公里。垃圾的运输成本非常惊人。 地处贫困地区,当地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在乡镇进行垃圾处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垃圾的产量在迅速增加,垃圾的消纳能力却无法提升。”全球环境研究所彭奎博士也意识到,青藏高原尤其是乡村地区,垃圾已经成了无法回避的大问题。
目前,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垃圾处理的方式都比较粗暴。“以致,现在我们只要一去到牧区的小城镇就能闻到一股垃圾焚烧的味道。”在杨欣看来,那是一种代表了当地城镇环境问题的特殊的气味标识。焚烧是为了减量,而剩下的垃圾则是被简单地填埋,少量才有机会运输到玉树州、格尔木的大型垃圾处理厂。彭奎尤其担心这种操作方式,“乡镇的填埋措施是最简易的,没有防渗等技术保障,等于给那块地区长久地埋下了污染源”。
发掘当地百姓的保护动力
两年前,全球环境研究所在进行社区参与保护的工作时,在玉树毛庄乡开展了一个实验性项目。彭奎表示,这个项目的目标就是为草原乡村生活垃圾处理探索出一个示范化的流程,教育当地百姓如何清理、分类、转运垃圾,并与当地政府机构对接最终的处理环节。 比如,要求毛庄乡在各种大型活动期间以及在学校定期开展环境教育,组建乡环保队伍,由成员们定期在固定的几条流域内清理、收集垃圾,集中进行分类和回收等。项目团队还在为村民制作垃圾清理、分类、回收的操作手册。 这种从内部发掘当地百姓保护动力,使其主动参与环境治理的做法是比较有效的。曲麻莱县就是一个案例。
现任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区曲麻莱县管理处资源管理局局长的尕塔,在当地是出了名的“环保卫士”。他从2010年任曲麻河乡党委书记时期,就开始探索一套垃圾解决方案。他认为,解决垃圾问题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地在源头实现减量。所以,他分别从科学和宗教两个层面对当地百姓进行教育,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对垃圾食品的消费。他在三个村各自成立了环保协会,指导村民们按照资源垃圾、大型垃圾、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有害垃圾等种类进行垃圾分类收集、分类填埋。每月会组织100人左右的马队、200人左右的摩托车队开展巡山清理垃圾。生态管护员每15天在公路沿线清理一次垃圾,每次30公里左右。
让杨大荣记忆颇深的,是一位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聘请的生态管护员索南达杰。他的家单村独户,离村公所和乡政府有60多公里。每星期他都要在管辖的寻护地段巡查1~2次,每次步行80多公里,常常是一个人在零下10至零下20多摄氏度的荒郊野外露宿。2017年,他顺着金沙江边,沿路捡回了40多公斤塑料、罐头瓶等垃圾,背了整整三天,才交到乡政府垃圾处理站。此外,尕塔组建了“54321”的系统化机制来用以保障各种环保措施的严格执行。县有监督员、乡有指导员、村有大队长、社有中队长、组有小队长,层层进行监督管理和指导;为了可以发挥不同群体的作用,他还在曲麻河乡各村组建了党员生态管护组、民兵生态管护组、妇女生态管护组、僧尼生态管护组4个小组;建立生态管护员摩托车队、马队和小车队;在每个村设置两户党员生态中心户;还有一支生态管护员大自然摄影队。
总之,让人人参与环境治理的模式,是为了提高当地百姓的环保积极性和责任意识。几年下来,曲麻莱县的垃圾问题得到了明显的控制。 但是,老百姓自发的保护行动几乎是不计代价的,其间产生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绝大部分是由他们自己承担。尕塔坦言,政府能够投入的资金非常有限,当地也几乎得不到外部资源的资助,垃圾回收变现严重缺乏。
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曲麻莱县当地的百姓尝试建立了一家绿色驿站,用于回收、转运村民的垃圾。它的特色在于,村民们交到驿站的废品类型都有明码标价,收入的70%可以在驿站的绿色超市换回日常消费品,剩下的30%可以获取现金。尕塔非常希望,这套实践证明有效的处理模式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从而在其他县乡进行推广。
垃圾治理不分你我
相比之下, 绿色江河探索的是另一条能与外部资源产生连接的路径。青藏公路是西藏道路运输的大动脉,数万货运车辆和旅行车辆都会行驶在这条道路上,并且留下随意丢弃的垃圾。2016年起,绿色江河与青海省政府合作,选择在青藏公路沿线建立垃圾回收站“青藏绿色驿站”,目前为止,这类驿站已经运行了五个。 驿站的模式,是由政府投资建设,民间机构负责管理运行。杨欣表示,垃圾处理必须首先拉动政府的积极性。
目前,“绿色驿站”一方面可以提供沿途车辆、司机短暂休息的空间,免费获取卫生间、热水、网络及充电服务。另一方面,鼓励司机和游客将产生甚至是主动拾到的垃圾留在“绿色驿站”里。生活在“绿色驿站”周围的农牧民,也可以把家中垃圾送到那里以换取生活用品。 驿站里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会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特别需要提到的是,青藏高原地区的货运是典型的单向运输,大部分离开西藏自治区的货车,都不会运载什么货物。因此,“绿色驿站”借助这部分被闲置的运输资源,鼓励司机们回程时带走一些需要转运的垃圾,送往城市集中处理。
杨欣提到,当地垃圾处理的难点是持续的资金支持不足,想要运行好这种模式,必须让“绿色驿站”实现自我造血的功能,这样也可以回馈政府的投入。那么,这就需要社会企业的积极参与,无论是购买广告,还是绿色产品、文创产品的销售分成。“当下,我们亟须让更多人了解‘绿色驿站’的存在和它所倡导的理念。”杨欣希望,进入青藏高原的人都能最终形成这样的习惯,生态出行、无痕出行。让垃圾清理、回收的行动成为青藏高原旅行的一种时尚。 只有“绿色驿站”获得成功的示范,它的模式也才有可能覆盖到更多城镇甚至是乡村道路,惠及更偏远的本地乡村居民。
彭奎在接受采访时,也非常强调社会力量参与的重要性。“青藏高原是全中国人的自然遗产,也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绝不仅仅是当地政府和百姓的责任。快消产品大量输入青藏高原,鉴于当地重要的生态地位,企业在获得回报的同时,是否应该为支持当地的垃圾回收贡献一点力量,或是对进入这一地区的消费品包装进行改造创新。这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可以思考的问题。”两年前,目睹过三峡大坝周边惊人的河流垃圾体量,杨大荣同样希望生活在高原之外的人们都能真正意识到,河流源头的垃圾生产绝不是与我们无关的,它的治理需要我们所有人的支持!
一万人=5~6吨垃圾
杨大荣在青藏高原野外工作的时间已经持续了近40年,他熟悉那里的生态环境,以及它们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的改变。 大概自2002年以后,杨大荣经过西藏、青海、云南等地,草原、神山甚至冰川地区的垃圾数量显著增加,特别是在那些知名的旅行圣地。杨大荣最熟悉的还是冬虫夏草的分布区。“四年前最严重的时候,约50平方公里的山区面积,如果大部分长有虫草,平均1万多人的采集队伍,一个多月下来,至少会产生5~6吨的生活垃圾。”他放眼望去,草原上遍地是方便面包装袋、罐头、饮料瓶、啤酒瓶、废弃的衣物等等。甚至到了第二年,有些塑料垃圾仍滞留在原地。
玉树地区,老百姓80%的收入来源于虫草,虫草分布区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当地百姓的生计。不仅如此,杨大荣也越发担心,“亚洲水塔”的生态地位将受到影响。因为,虫草核心分布地带就处于长江、黄河、澜沧江、雅鲁藏布江、怒江、雅砻江等大江源头的高寒草甸,大风、降雨会将草原垃圾直接带入河流体系。 最近四五年里,杨大荣的一部分重要工作就是参与青藏高原地区的社区教育活动。今年5月,他受邀来到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对职工、学生、社、区、村群众开展了环境生态保护和科学采挖冬虫夏草等的学术报告,同时参加了他们的社、区、村的调查与宣传活动。
5~7月是采挖虫草和中药材的季节,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区资源管理局80%的工作人员都出发野外工作,把成吨的垃圾带回县、乡统一处理;曲麻莱县巴干乡团结村党支部书记才闹,一个月有3到5次,每天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爬行40多公里,边捡垃圾边开展宣传;30多岁的康巴汉子九美昂布,会和幼儿园的小朋友、学校师生一起把野外捡回的塑料袋、罐头盒子、牛羊毛等做成各种各样的民族工艺品,有些工艺品已经外销……半个多月的曲麻莱之行让杨大荣惊喜地看到了一些转机。而他在意的是,高原之外,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当地百姓为“亚洲水塔”生态保护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更不会了解他们依然面临的垃圾处理的巨大困境。
垃圾回收转运缺位
杨欣所在的“绿色江河”可以说是国内非常早注意到高原垃圾处理难题的民间环保机构。早在2002年,绿色江河资助的一项大学生志愿者调查活动发现,在青藏公路沿线,平均每隔十米就会出现一件塑料垃圾,一公里就是一百件。此后,绿色江河持续八年对青藏公路沿线、青藏线长江源区集镇垃圾状况进行了调查。青藏铁路、公路的通车为高原旅游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外来人口在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可估量的垃圾。重要的是,城市的消费方式正在高原快速渗透。包装食品和饮料已经成为了高原老百姓的一种消费时尚。
“但一直以来,高原传统的生活方式几乎不产生需要专业处理的垃圾,老百姓也没有垃圾处理的习惯。”杨欣表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青藏高原地区除主要城市以外,始终没有垃圾分类回收、转运、处理的体系。 这也与高原地区分散的居住方式有关。在那里,一个行政村的面积可达几百平方公里,村子里每户牧民家庭之间的距离30~40公里,最近的也有5~6公里。垃圾的运输成本非常惊人。 地处贫困地区,当地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在乡镇进行垃圾处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垃圾的产量在迅速增加,垃圾的消纳能力却无法提升。”全球环境研究所彭奎博士也意识到,青藏高原尤其是乡村地区,垃圾已经成了无法回避的大问题。
目前,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垃圾处理的方式都比较粗暴。“以致,现在我们只要一去到牧区的小城镇就能闻到一股垃圾焚烧的味道。”在杨欣看来,那是一种代表了当地城镇环境问题的特殊的气味标识。焚烧是为了减量,而剩下的垃圾则是被简单地填埋,少量才有机会运输到玉树州、格尔木的大型垃圾处理厂。彭奎尤其担心这种操作方式,“乡镇的填埋措施是最简易的,没有防渗等技术保障,等于给那块地区长久地埋下了污染源”。
发掘当地百姓的保护动力
两年前,全球环境研究所在进行社区参与保护的工作时,在玉树毛庄乡开展了一个实验性项目。彭奎表示,这个项目的目标就是为草原乡村生活垃圾处理探索出一个示范化的流程,教育当地百姓如何清理、分类、转运垃圾,并与当地政府机构对接最终的处理环节。 比如,要求毛庄乡在各种大型活动期间以及在学校定期开展环境教育,组建乡环保队伍,由成员们定期在固定的几条流域内清理、收集垃圾,集中进行分类和回收等。项目团队还在为村民制作垃圾清理、分类、回收的操作手册。 这种从内部发掘当地百姓保护动力,使其主动参与环境治理的做法是比较有效的。曲麻莱县就是一个案例。
现任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区曲麻莱县管理处资源管理局局长的尕塔,在当地是出了名的“环保卫士”。他从2010年任曲麻河乡党委书记时期,就开始探索一套垃圾解决方案。他认为,解决垃圾问题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地在源头实现减量。所以,他分别从科学和宗教两个层面对当地百姓进行教育,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对垃圾食品的消费。他在三个村各自成立了环保协会,指导村民们按照资源垃圾、大型垃圾、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有害垃圾等种类进行垃圾分类收集、分类填埋。每月会组织100人左右的马队、200人左右的摩托车队开展巡山清理垃圾。生态管护员每15天在公路沿线清理一次垃圾,每次30公里左右。
让杨大荣记忆颇深的,是一位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聘请的生态管护员索南达杰。他的家单村独户,离村公所和乡政府有60多公里。每星期他都要在管辖的寻护地段巡查1~2次,每次步行80多公里,常常是一个人在零下10至零下20多摄氏度的荒郊野外露宿。2017年,他顺着金沙江边,沿路捡回了40多公斤塑料、罐头瓶等垃圾,背了整整三天,才交到乡政府垃圾处理站。此外,尕塔组建了“54321”的系统化机制来用以保障各种环保措施的严格执行。县有监督员、乡有指导员、村有大队长、社有中队长、组有小队长,层层进行监督管理和指导;为了可以发挥不同群体的作用,他还在曲麻河乡各村组建了党员生态管护组、民兵生态管护组、妇女生态管护组、僧尼生态管护组4个小组;建立生态管护员摩托车队、马队和小车队;在每个村设置两户党员生态中心户;还有一支生态管护员大自然摄影队。
总之,让人人参与环境治理的模式,是为了提高当地百姓的环保积极性和责任意识。几年下来,曲麻莱县的垃圾问题得到了明显的控制。 但是,老百姓自发的保护行动几乎是不计代价的,其间产生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绝大部分是由他们自己承担。尕塔坦言,政府能够投入的资金非常有限,当地也几乎得不到外部资源的资助,垃圾回收变现严重缺乏。
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曲麻莱县当地的百姓尝试建立了一家绿色驿站,用于回收、转运村民的垃圾。它的特色在于,村民们交到驿站的废品类型都有明码标价,收入的70%可以在驿站的绿色超市换回日常消费品,剩下的30%可以获取现金。尕塔非常希望,这套实践证明有效的处理模式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从而在其他县乡进行推广。
垃圾治理不分你我
相比之下, 绿色江河探索的是另一条能与外部资源产生连接的路径。青藏公路是西藏道路运输的大动脉,数万货运车辆和旅行车辆都会行驶在这条道路上,并且留下随意丢弃的垃圾。2016年起,绿色江河与青海省政府合作,选择在青藏公路沿线建立垃圾回收站“青藏绿色驿站”,目前为止,这类驿站已经运行了五个。 驿站的模式,是由政府投资建设,民间机构负责管理运行。杨欣表示,垃圾处理必须首先拉动政府的积极性。
目前,“绿色驿站”一方面可以提供沿途车辆、司机短暂休息的空间,免费获取卫生间、热水、网络及充电服务。另一方面,鼓励司机和游客将产生甚至是主动拾到的垃圾留在“绿色驿站”里。生活在“绿色驿站”周围的农牧民,也可以把家中垃圾送到那里以换取生活用品。 驿站里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会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特别需要提到的是,青藏高原地区的货运是典型的单向运输,大部分离开西藏自治区的货车,都不会运载什么货物。因此,“绿色驿站”借助这部分被闲置的运输资源,鼓励司机们回程时带走一些需要转运的垃圾,送往城市集中处理。
杨欣提到,当地垃圾处理的难点是持续的资金支持不足,想要运行好这种模式,必须让“绿色驿站”实现自我造血的功能,这样也可以回馈政府的投入。那么,这就需要社会企业的积极参与,无论是购买广告,还是绿色产品、文创产品的销售分成。“当下,我们亟须让更多人了解‘绿色驿站’的存在和它所倡导的理念。”杨欣希望,进入青藏高原的人都能最终形成这样的习惯,生态出行、无痕出行。让垃圾清理、回收的行动成为青藏高原旅行的一种时尚。 只有“绿色驿站”获得成功的示范,它的模式也才有可能覆盖到更多城镇甚至是乡村道路,惠及更偏远的本地乡村居民。
彭奎在接受采访时,也非常强调社会力量参与的重要性。“青藏高原是全中国人的自然遗产,也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绝不仅仅是当地政府和百姓的责任。快消产品大量输入青藏高原,鉴于当地重要的生态地位,企业在获得回报的同时,是否应该为支持当地的垃圾回收贡献一点力量,或是对进入这一地区的消费品包装进行改造创新。这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可以思考的问题。”两年前,目睹过三峡大坝周边惊人的河流垃圾体量,杨大荣同样希望生活在高原之外的人们都能真正意识到,河流源头的垃圾生产绝不是与我们无关的,它的治理需要我们所有人的支持!